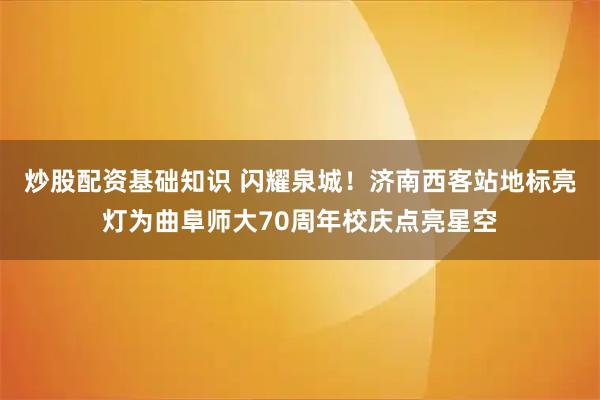城市更新中零星地块的立法实现路径与制度创新炒股配资基础知识
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,在存量规划时代具有重要意义。零星地块作为城市更新中的特殊类型,具有分布散、面积小、权属复杂等特点,其开发改造需要特殊的立法设计与制度安排。本文将从零星地块的立法定位、规划整合、实施机制、权益平衡及配套政策五个维度,系统分析城市更新中零星地块的立法实现路径,并结合上海、南宁等地的实践经验,探讨如何通过立法创新破解零星地块开发难题,为完善城市更新法律体系提供参考。
零星地块在城市更新立法中的定位与挑战
零星地块通常指在城市建成区内散布的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等小规模未利用或低效利用土地,这些地块因面积狭小或形状不规则而难以独立开发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"下半场",如何通过立法手段激活这些"城市碎片"成为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关键议题。从立法层面界定零星地块并明确其法律地位,是构建城市更新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工作。
展开剩余88%当前我国各地对零星地块的立法定义存在一定差异,但核心要素基本一致。《南宁市"零星地块"协议出让管理办法》将其纳入规范性文件管理范畴,而自然资源部2023年《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》则从功能角度将其描述为"难以独立开发的零星地块",并允许与相邻产业地块整合开发。上海市在《城市更新条例》实施后制定的配套细则中,进一步将零星更新项目定义为"基于物业权利人的意愿,由物业权利人等各类市场主体根据规划和相关规定实施"的更新类型。这些定义反映了零星地块在立法中的三个基本属性:规模零散性(单宗面积通常不超过3亩)、开发依附性(需与相邻地块整合)和权属复杂性(涉及多方主体)。
零星地块立法面临多重挑战:一是产权碎片化导致整合难度大,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混杂;二是规划适配性要求高,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预留弹性;三是利益平衡机制不完善,权利主体诉求多样;四是审批程序复杂,涉及规划调整、土地供应等多环节。针对这些挑战,立法需要构建从地块认定、规划整合到实施保障的全链条制度框架,为不同类型的零星地块更新提供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。
规划统筹与土地整合的立法创新
零星地块的有效利用首先依赖于规划层面的统筹安排和创新设计。传统规划管理模式下,零星地块因达不到独立开发门槛常被闲置或低效利用,而现代城市更新立法正通过多种机制打破这一困境。
弹性规划机制是破解零星地块规划适配难题的关键。自然资源部171号文明确提出,对难以独立开发的零星地块,“可与相邻产业地块一并出具规划条件,整体供应给相邻产业项目用于增资扩产”。这种方法突破了宗地界限,允许在规划条件中"捆绑"处理零星地块与主体地块,为整合开发提供制度通道。上海市在《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》中进一步细化了这种"规划打包"模式,通过容积率奖励、功能混合等激励措施,鼓励市场主体主动整合周边零星地块。
土地整合政策方面,各地立法探索了多样化的路径。南宁市采用"协议出让"方式处理零星地块,简化了土地供应程序;而自然资源部则创新性提出"凭证置换"机制,允许"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之间按照面积相近或价值相当、双方自愿原则进行置换"。这种产权置换制度为不同性质土地间的整合提供了法律依据,特别适用于城乡结合部等权属复杂区域的零星地块更新。
规模控制标准也是立法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。相关政策规定,零星地块"原则上单宗面积不超过3亩,累计不超过再开发项目用地总面积的10%",但同时也预留了例外条款,“经论证确实无法单独开发的可适当放宽限制”。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规定,既防止了零星地块无序扩张,又为特殊情形下的合理变通提供了空间。立法实践中,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明确具体标准和操作流程。
多元实施机制与主体权益保障
零星地块更新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推进机制,并在立法中妥善平衡各方主体权益。与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不同,零星地块更新通常难以采用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,而需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。
市场主体主导机制日益受到立法重视。上海市将"零星更新项目"明确定义为"基于物业权利人的意愿,由物业权利人等各类市场主体"实施的更新类型。这种自下而上的更新模式强调产权人的自主决策权,政府主要发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。立法通过明确实施主体资格和权利义务,为市场主体参与零星地块更新提供了制度保障,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。
协议实施机制是协调多方利益的重要法律工具。《南宁市"零星地块"协议出让管理办法》专门规范了通过协议方式出让零星地块的程序和条件。协议机制强调平等协商和意思自治,特别适用于权属关系复杂、难以通过强制手段整合的零星地块更新。立法实践中,需要进一步细化协议达成的程序规则、内容要求和争议解决机制,确保协议过程的公平、透明和高效。
权益保障与利益分配是零星地块立法的核心问题。一方面,立法需要保护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,如上海市《城市更新条例》强调更新必须"基于物业权利人的意愿";另一方面,也需要建立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,平衡公共利益、开发商利益和原权利人利益。自然资源部提出的"价值相当"置换原则,为产权调整中的利益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。立法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估、公开听证等程序性规定,确保利益分配的公正性。
针对不同更新情形,立法应设计差异化的实施路径:对于与主体项目紧密关联的零星地块,可采用"整体供应"方式;对于权属相对独立的零星地块,可适用简化版的更新程序;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零星地块,则可设立专门的协调解决机制。通过多层次制度设计,满足不同类型零星地块更新的需求。
配套政策与程序优化
零星地块更新的顺利推进离不开配套政策支持和程序优化。立法不仅需要确立基本规则,还需构建促进更新的政策工具箱和高效便捷的管理流程。
激励性政策是推动零星地块更新的重要杠杆。容积率奖励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,允许开发主体在整合零星地块后获得一定的容积率补偿。此外,还可包括税费减免、地价优惠、功能混合许可等激励措施。上海市在《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》中系统集成了各类激励政策,形成"政策包"效应。立法可将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,提高其稳定性和权威性。
审批程序简化对零星地块更新尤为关键。传统用地审批流程复杂、周期长,与零星地块更新"小而快"的特点不相适应。立法应推动建立"绿色通道",整合规划许可、用地审批、建设管理等环节,推行并联审批和限时办结制度。对于特定类型的零星地块更新,还可探索备案制、告知承诺制等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。南宁市通过专门《办法》规范零星地块协议出让程序,体现了程序优化的立法思路。
标准规范制定有助于提高零星地块更新的质量和效率。立法可授权相关部门制定零星地块认定的技术标准、整合开发的设计规范、价值评估的方法准则等配套标准,为实践操作提供统一依据。特别是对于"面积相近或价值相当"的置换原则,需要进一步细化操作标准,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的执行偏差。
试点容错机制也是立法应考虑的重要内容。自然资源部171号文明确将零星地块改革纳入"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"范围,鼓励地方探索创新。立法可建立容错免责条款,允许试点地区在程序简化、政策突破等方面进行尝试,为全国性制度完善积累经验。同时建立试点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,确保改革风险可控。
立法趋势与制度展望
从国内外实践看,城市更新中的零星地块立法呈现若干明显趋势,未来制度发展需要顺应这些趋势,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。
专项立法与综合立法相结合是值得关注的方向。目前零星地块规定散见于各类法规政策中,如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作为综合立法包含原则性规定,而《南宁市"零星地块"协议出让管理办法》则是专门规范。未来立法可考虑在综合性城市更新法规中设立零星地块专章,同时鼓励地方制定专门规章或实施细则,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。
产权制度创新将进一步深化。零星地块更新的核心障碍是产权碎片化,未来立法需在现有"凭证置换"基础上,探索更多产权整合工具,如共有产权、时序产权、空间权分割等灵活多样的产权安排。特别是要破解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之间的制度壁垒,建立统一的产权流转市场。
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应用将为零星地块更新提供技术支持。通过城市信息模型(CIM)、地理信息系统(GIS)等技术,建立零星地块数据库和动态监测系统,实现地块识别、规划整合、项目监管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。立法应鼓励技术创新,同时规范数据采集、共享和使用行为。
从更长远看,零星地块立法应放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考量。2022年12月上海市制定的《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》体现了从"管理"向"治理"的转变趋势,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。未来立法应进一步强化社区参与、公众协商等治理机制,使零星地块更新不仅改善物质环境,也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社区活力提升。
综上所述,城市更新中零星地块的立法实现需要系统构建从规划整合、实施机制到配套政策的制度体系,在法治轨道上激活这些"城市边角料"的价值。通过立法创新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,对于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未来立法应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和创新思维,为零星地块更新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发布于:江苏省美港通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